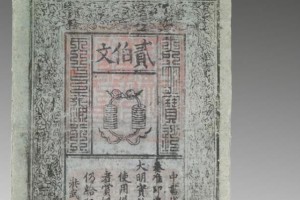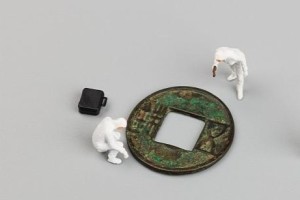曹冲【东汉末年神童、曹操之子】 – 人物百科
04/19
努尔哈赤【清王朝的奠基者】 – 人物百科
04/19
皇太极【建立大清的有为之君】 – 人物百科
04/19
刘表【东汉末年名士、汉末群雄之一】 – 人物百科
04/19
荀攸【东汉末年曹操谋士】 – 人物百科
04/19
羊角哀,战国时燕人,生卒年不详,与左伯桃为友,闻楚王善待士,同赴楚,值雨雪粮少,伯桃遂并衣食与哀,入树中死,哀独行仕楚,显名当世,启树发伯桃尸改葬之,后亦自杀,
秦昭襄王(前325年-前251年),一称秦昭王,嬴姓,赵氏,名则,又名稷,秦惠文王之子,秦武王异母弟,战国时期秦国国君,早年在燕国做人质,公元前307年,秦武王去世,秦昭襄王与其弟争位,遂立,公元前306年—前251年在位,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,在位时,秦国继续扩张,最著名的、决定秦赵两国命运的长平之战,就是在秦昭王在位晚期发生的,秦昭襄王在位初期,由其母宣太后当权,外戚魏冉为宰相,史称“王少,宣太后自治事,任魏冉为政,威震秦国”,魏冉推荐白起为将军,先后战胜三晋、齐、楚等国,取得魏国的河东
屠岸贾(gǔ),屠岸姓,名贾,在戏剧和民间传说中,屠岸贾一直是以一个大奸臣的面目出现的,元代作家纪君祥创作的《赵氏孤儿》杂剧,影响深远,以后的许多剧种都据此编出了精品剧目,多年流传,屠岸贾也因此而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奸臣形象,
豹尾一词从古至今有多种解释,现归纳总结六点释义,仅供参考1.豹的尾巴 2. 天子属车上的饰物,悬于最后一车 3. 借指天子属车,即豹尾车 4. 旧时阴阳五行家谓旌旗之象 5. 比喻乐曲、诗文坚劲有力的结尾部分 6. 阴神名,“四大阴帅“之一【词语】:豹尾【注音】:bào wěi【出处】: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
顾小失大【顾小失大的意思】- 成语大全
07/11
顾全大局【顾全大局的意思】- 成语大全
07/11
顾后瞻前【顾后瞻前的意思】- 成语大全
07/11
顾后瞻前【顾后瞻前的意思】- 成语大全
04/25
顾复之恩【顾复之恩的意思】- 成语大全
04/25
毛利胜永是谁?他一生当中拥有着哪些功绩?_世界古代史 菊江历史网
2024年4月22日
320阅读
历史上的阿提拉是一个怎样的人?真的是恶魔印象吗?_世界古代史 菊江历史网
2024年4月22日
300阅读
平将门是谁?为何说他是日本平安时代四大怨灵之一?_世界古代史 菊江历史网
2024年4月22日
383阅读
奥古斯丁是什么时候的人_世界古代史 菊江历史网
2024年4月22日
321阅读
《十二表法》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罗马共和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_世界古代史 菊江历史网
2024年4月22日
332阅读